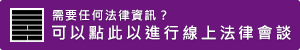刑法第五十七條規定註釋-刑罰之酌量
刑法第57條規定:
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
一、犯罪之動機、目的。
二、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三、犯罪之手段。
四、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
五、犯罪行為人之品行。
六、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
七、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
八、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
九、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十、犯罪後之態度。
說明:
科刑(或稱刑罰裁量、量刑等)之標準與科刑之基礎,二者之關係至為密切,在適用上,對於犯罪行為事實論罪科刑時,須先確認科刑之基礎,始得進而依科刑之標準,諭知被告一定之宣告刑。而責任原則,不僅為刑事法律重要基本原則之一,且為當代法治國家引為科刑之基礎。現行法僅就科刑之標準予以規定,並未對科刑之基礎設有規範。
為使法院於科刑時,嚴守責任原則,爰仿德國刑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第四十八條第一項之立法例,明定以行為人之責任為科刑之基礎。本條所定刑罰酌科之一般標準中第一款「犯罪之動機」與第二款「犯罪之目的」乃故意犯專設之事項,予以合併改訂於第一款。
現行第八款之科刑標準,範圍較狹,僅包括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平日有無恩怨、口角,或其他生活上之關係;惟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在犯罪行為上之關係,則不在其內。矧按犯罪之原因,常與犯罪行為人及被害人間,在行為時之互動密切相關,例如,在竊盜案件中,被害人之炫耀財產,常係引起犯罪行為人覬覦下手之原因。此種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在犯罪行為上之關係,亦屬科刑時應予考量之標準,爰將「平日」一語刪除,使其文義範圍,亦得包含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在犯罪行為上之關係;並將其款次改列為第七款。
邇來處罰違反義務犯罪之法規日益增多(如電業法第一百零七條),而以違反注意義務為違法要素之過失犯罪發生率,亦有增高趨勢(如車禍案件,醫療糾紛案件),犯罪行為人違反注意義務之程度既有不同,其科刑之輕重,亦應有所軒輊,又就作為犯與不作為犯(如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條)而言,其違反不作為義務或作為義務之程度,亦宜審酌以為科刑之標準。爰參酌德國立法例(刑法第四十六條(2)增訂第八款規定「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以利具體案件量刑時審酌運用。
關於刑法第57條所列科刑情狀之事實,諸如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等,不以經過嚴格證明為必要,不同於犯罪構成要件所關之事實,自無許當事人就此自由證明事項,任意指摘法院違反嚴格證據調查職責之要求(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301號刑事判決)。
按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75年台上字第7033號及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
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罰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並賦予法院以裁量權,以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565號、90年度台上字第4636號裁判意旨參照)。又刑之量定,固為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但此項職權之行使,仍應受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罪刑相當原則之支配,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應行注意事項及一切情狀為之,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符合法律授權之目的,此即所謂自由裁量權之內部界限(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357號、97年度台上字第6874號判決意旨參照)。
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罰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此所以刑法第五十七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十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而現階段之刑事政策,非祇在實現以往應報主義之觀念,尤重在教化之功能,立法者既未將殺人罪之法定刑定為唯一死刑,而將無期徒刑及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列為選科之項目,其目的即在賦予審判者能就個案情狀,審慎斟酌,俾使尚有教化遷善可能之罪犯保留一線生機。故法院對於泯滅天性,窮兇極惡之徒予以宣告死刑之案件,除應於理由內就如何本於責任原則,依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定各款審酌情形,加以說明外,並須就犯罪行為人事後確無悛悔實據,顯無教化遷善之可能,以及從主觀惡性與客觀犯行加以確實考量,何以必須剝奪其生命權,使與社會永久隔離之情形,詳加敘明,以昭慎重(最高法院九十五年度台上字第六五六五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罰係對犯罪行為人之生命、自由及財產之拘束、剝奪,行為人所受之刑罰,應與法律所保護之利益,及行為人侵害該法益之程度相當,始符合比例原則。死刑乃刑罰之最嚴厲手段,犯罪行為縱屬重大,倘行為人仍有再教育、再社會化之可能,遽以死刑論科,即與刑罰之本旨不符(最高法院九十四年度台上字第四一四六號判決意旨參照)。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2分之1。」係以成年之行為人所教唆、幫助、利用、共同犯罪或其犯罪被害者之年齡,作為加重刑罰之要件,雖不以該行為人明知(即確定故意)上揭諸人的年齡為必要,但至少仍須存有不確定故意,亦即預見所教唆、幫助、利用、共同實行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之人,係為兒童或少年,而不違背其本意者,始足當之。此項刑罰加重事由,自應於理由欄詳予載明並說明所憑之依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3559號刑事判決)。
刑法規定之各犯罪類型所保護之法益,固有個人法益、社會法益及國家法益之別,惟就刑罰法規本具有維護社會秩序及人類共同生活安全之基本目的而言,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及該條第九款所謂之「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自不以各該犯罪之刑罰規定所直接保護之法益為限。又量刑固不必然因被害人為本國人或外國人而有輕重之別,然事實審法院於具體個案之科刑,考量被告之犯行於國家尊嚴、形象所生之損害,本質上仍不失為就該犯行對社會秩序或共同生活安全之損害所為之斟酌,其綜合其他犯罪之一切情狀,整體審酌而為之量刑結果,倘未逾越法定刑度,又與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無違,即難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574號刑事判決)。
查:遲來的正義,已非正義,案件延宕多時未結,非但有時真相難明,於訴訟當事人而言,必然遭受往返法院之身體勞累,不能安心工作,既造成經濟損失,又心理煎熬,多所折磨,乃不言而喻,不待贅言者。自西元一九六六年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四條第三項第三款首先揭示被告有權立即受審判,不得無故稽延之原則後,多種國際公約漸加採認,美、日諸國亦將之入憲,殆成普世價值,我國透過司法院釋字第四四六及五三○號解釋,同謂人民享有受法院公正、合法與迅速審判之權利,嗣並將首揭國際公約循立法程序,使之具有國內法之效力,更制定刑事妥速審判法予以保障,參酌追訴時效法理,承認正義刑罰理論,對於遭受結案延滯訟累之有罪被告,給予減刑寬遇,彌補其身心、經濟損害,觀諸該法第一條、第七條規定和立法理由甚明。依此第七條規定,其適用固應審酌「訴訟程序之延滯,是否係因被告之事由。案件在法律及事實上之複雜程度與訴訟程序延滯之衡平關係。其他與迅速審判有關之事項」,是若案件之延宕,非因被告個人事由所致,此不利結果之發生,當由國家承受;而能否歸咎被告,依同法第三條「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其他參與訴訟程序而為訴訟行為者,應依誠信原則,行使訴訟程序上之權利,不得濫用,亦不得無故拖延」之反面意旨,倘於客觀上,足以認為被告方面係基於訴訟防禦權之正當行使,即無不可。又上揭第七條各款所定者,係法院於酌量減輕被告刑罰之前,所應審酌之事項,屬於法定刑之減輕;一旦裁量認為有其適用,於擇定宣告刑時,再依刑法第五十七條規定之各量刑因素斟酌處理,二者範疇有別;至刑法第五十八條關於酌量加重罰金數額之規定,乃僅罰金刑部分有其適用,不及於其他種類之刑罰,係專就犯罪所得利益和法定刑罰金部分相為比較,賦予法院裁量權,俾妥適衡量、實現正義,不生既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七條酌減其刑,復按刑法第五十八條酌加罰金數額,而有前後矛盾之問題。本件經檢察官起訴列為被告者,多達三十餘人,卷宗一百餘,外附證物數大袋,案情多樣,檢察官就此兼有一人犯數罪,及數人共犯一罪和數罪之相牽連案件,合為一件提起公訴,雖不違反刑事訴訟法第七條規定,但卷證盈櫃,確實存在法律與事實之複雜性,程度非輕,羅福助、林錦源、吳永祥在審判中,聲請傳喚謝裕民、陳建霖及張哲發到庭踐行交互詰問程序,微論人數非多,庭期亦少,張哲發更為第一審之共同被告,實乃訴訟防禦權之正當行使,林錦源在審判中翻供,亦不能逕認延滯訴訟之進行。原審以本件審判歷時逾八年,衡酌其複雜程度、罪名輕重、所致經濟與心理負擔等各情,認有刑事妥速審判法第七條規定之適用,然於併科罰金刑部分,則依刑法第五十八條規定處理,經核無非係法院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存有違誤,容有誤會(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422號刑事判決)。
刑之量定,亦屬事實審法院之自由合理裁量事項,法院本得於法定刑或處斷刑所劃設框架內,於現存法秩序內部,進行「法的發現」及「法的創造」,據以評價具體個案,進行合理裁量。因此,量刑本身原即具有一定之幅度,於此合理幅度內均尚難認為不相當,除非事實審法院之裁量逾越合理範圍,失諸過輕或過重,上訴審法院為實現具體分配正義,確保法的安定性或法的平等性,始得撤銷改判,更正第一審法院之量刑不均衡判斷。既然決定責任刑範圍之指標為該當犯罪行為本身(個別行為責任說),犯行後事情由於是犯罪終了後之事情,原則上對於責任刑之範圍(幅度)固無直接關係,但因處罰犯罪根據在於特定行為違法侵害法益,或紊亂法秩序,行為人於實施犯行後之特定行為、態度如有助於回復被侵害之法益或受攪亂之法秩序,縱令已屬事後之舉,似仍非不得將行為人之犯行後行為、態樣,當成與減輕過去犯罪行為違法性或責任程度,具有同等之價值看待。尤其,被告如於偵查或審理中自白犯行,不僅得使偵查、公判審理活動迅速進展,國家得將有限司法資源有效投入其他犯罪之偵審程序,再者,不管是對於犯罪被害人,或是對於一般社會來說,也可以實現儘早解決訟案之安心感,準此以觀,至少從一般預防或司法政策觀點加以考量,針對自白之被告,於量刑時有利考量自白該項因子,應難認無相當之理由,尤其,在責任刑幅度較為寬廣之犯罪,犯行後之自白態度,對於量刑確難認無相當程度之作用力(川合昌幸,〈被告人反省態度等量刑〉,判例1268號,2008年7月15日,第49頁至第54頁參照)。又我國及日本刑法,立法者規定相當幅度之法定刑度,針對被包攝於各個刑罰法條之各種犯罪類型,將具體可罰性之高低階層採取委諸於法院判斷之模式,法院除應反映社會實質違法評價及刑罰感覺等外,尤應審酌該當構成要件所設定之犯罪態樣、手段、動機、結果、法益及保護法益等等,將特定之犯罪事實對應責任重輕予以區分排列,並綜合具體個案之整體性,決定可罰性之程度。因此,法院在立法者所劃定之法定刑幅度內,考量刑罰之目的(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最終決定具體量刑時,既係在立法者所劃設之「量的(幅的)」容許領域內,除非有違背責任原則,濫用裁量權限等情事外,於一定幅度內之量刑,應難認有背於罪刑相當原則(遠藤邦彥,〈量刑判斷過程總論檢討【第1回】〉,判例1183號,2005年9月15日,第20頁;〈量刑判斷過程總論檢討【第2回】〉,判例1185號,2005年10月1日,第38頁、第39頁)。按被害人由馬車跳下,橫汽車路跑過,亦屬不無過失,雖上訴人欠缺注意停車不及,將其撞傷身死,是為被害人致死之主要原因,不能影響於上訴人犯罪之成立,然被害人既與有過失,自應量處較輕之刑(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1664號判例參照),蓋因被害人行動之競合介在,而招致發生重大結果時,相較於被害人無過失案型,加害人形成反對動機之餘裕較為收縮,期待可能性較為減弱,自應相應其責任程度妥適量刑…刑事審判乃係由偵查至矯正之刑事整體程序之其中一環,刑事司法之窮極目的既在於使社會遠離犯罪,為此刑事審判除應考量應報刑之觀點外,更不得輕忽預防之視點。尤其於刑事審判更不得無視個別被告之特別預防觀點。又特別預防之核心終究應求諸於特定被告發自於衷心之反省,並冀圖藉此防止再犯。準此,於刑事審判應不得完全無視行為人之自白反省悔悟態度,法院於量刑時,行為者之自白犯後態度,亦得作為量刑考量因子之一…按犯罪行為之處罰根據,在於犯罪行為違法侵害法益,或紊亂法秩序,行為人之犯後特定行為或態度,如有積極試圖回復受侵害之法益或受攪亂之法秩序時,則非不得將行為人之犯後行為或態度,評價為具有減輕過去犯罪行為之違法性或責任程度之價值,是被告林芝妤於事故甫發生後,停留於事故現場並積極前去關心被害人狀況,積極試圖回復受侵害之法益或受攪亂之法秩序,參照前開說明,應得將其犯後行為或態度,評價為具有減輕過去犯罪行為之違法性或責任程度之價值,應非不得將其積極關心詢問被害人狀況之行為、態度作為有利量刑因子(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6年度原交上易字第7號刑事判決)。
量刑之輕重,係法院就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遽予評斷。刑法第57條第10款所稱犯罪後之態度,包括行為人犯罪後有無悔悟等情形,足以測知其刑罰適應性之強弱。被告坦承犯行,不惟可以減省訴訟勞費,更屬其人格更生之表徵,自可予科刑上減輕之審酌。如被告否認犯罪,係其辯解權之行使,倘以此作為犯罪後毫無悔意、態度不良之評價,並資為量刑畸重標準之一,而明顯有裁量權濫用之情形者,固為法所不許,但就個案量刑審酌之情狀為整體綜合之觀察,苟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包括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為之觀察,倘其刑之量定未逾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亦不生量刑畸重之裁量權濫用,即不得僅因判決書記載「事後否認犯行之態度,毫無悔意」等用語文字,即認係將被告行使抗辯權之內容作為量刑標準之審酌(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62號刑事判決)。
瀏覽次數:17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