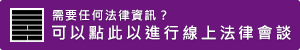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規定註釋-普通殺人罪
刑法第271條規定: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按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第1、2項定有明文。是刑法上之故意,分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又按殺人與傷害致人於死之區別,應以加害人有無殺意為斷,不以兇器種類及傷痕之多寡為絕對標準,亦不能因與被害人素不相識,原無宿怨,事出突然,即認為無殺人之故意。又下手之情形如何,於審究犯意方面,為重要參考資料,故認定被告是否有殺人犯意,自應審酌當時情況,視其下手之輕重、加害之部位等,以為判斷之準據(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1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申言之,行為人犯罪時內心之主觀犯意,非他人輕易即得察覺,故加害人之行為,究屬基於殺人之犯意或僅係傷害之故意,應詳查審認案內所有事證,深入觀察被害人受傷之情形、部位、加害人下手之方法、輕重、犯後態度等因素予以綜合評析(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8年度矚上重訴字第538號刑事判決)。
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一項之殺人罪,其構成要件有二:第一須有殺害之行為,係指行為人以非法方法,故意戕害他人生命之謂,亦即凡其行為足以使人喪失生命發生死亡結果者,皆屬之。第二所殺者,須為人,且為行為人以外具有生命力之自然人。申言之,殺人罪之成立,除行為人有殺人之主、客觀犯意及行為外,尚必須確有被害人其人,且有死亡之事實,始克當之。本件檢察官起訴書記載上訴人除射殺劉有誠外,同時在場與劉有誠同居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柬埔寨籍女子,亦遭上訴人持槍射擊死亡,而原判決事實認定該女子係越南籍成年女子,並以起訴書所載柬埔寨籍有誤,惟於理由內並未說明其依據,已有未合。且其事實認該女子係在上址與劉有誠同居之越南女子,亦與郭子俊於第一審證稱:「……那個女的不是劉有誠在越南的同居女人,那個是陪劉有誠過夜的女人,……」「因為那個女的拿到錢之後就可以走了,但是王加文還是把她殺了」等語相歧,乃有認定事實未依憑卷內證據之違誤。又本件既未發現該名女子之屍體或骨骸,卷內亦無相關資料可資參酌,則檢察官起訴書所指同時遭上訴人槍殺之女子,是否確已死亡?其真實身分及與劉有誠之關係為何?均有未明。此攸關上訴人該部分是否亦成立殺人犯罪之認定,自有詳加釐清之必要。乃原判決未就上情根究明白,即逕為不利上訴人之認定,殊嫌速斷(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406號刑事判決)。
死刑是否合憲及其相關問題:死刑立法之合憲審查:贊成或反對廢除死刑,乃無關對、錯之價值選擇,屬言論自由範疇。台灣係民主法治國家,對不同之言論,應互相尊重及包容。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下稱兩公約)施行法公布生效後,公政公約第6條所揭示之「廢除死刑目標」,雖已為我國成文法所設定之目標,然迄今仍僅止於「目標」,在全國達成共識,並經立法廢除死刑規定前,法院仍應依法審判,不得迴避死刑規定之適用。憲法第80條明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此「審判獨立」之憲法保障,以「法官依據法律」審判為前提,目的在確保代表人民集體意志所制定之法律,得有效貫徹、施行,俾落實主權在民之民主憲政原理。因此「審判獨立」僅係手段,不是最終目的。而所謂法律,係指具合憲性之法律。故依法制定、公布施行之法律,於法官(法院)依其合理確信,認有牴觸憲法之疑義時,固得停止審判,而聲請釋憲機關解釋,但若法官(法院)無合理確信認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則無停止審判聲請釋憲之必要。而於該法未經釋憲機關解釋為違憲並宣告無效前,尚不得拒絕適用。亦不得逾越立法論及解釋論分際,逕以「廢除死刑」之刑事政策目標,拒絕適用死刑規範。憲法明定我國係主權在民之民主國家,所有治權均來自人民之付託,司法審判權亦然。法官既係受人民之託付,依法行使司法審判權限,則其依此授權及公正審判程序,判處刑事被告法律所定之死刑刑罰,並非基於其個人身分或人格地位剝奪或否定他人人性尊嚴,自無違反憲法第7條平等原則問題。我國屬尚未廢除死刑之國家,本案應適用之死刑規定即刑法第33條第1款及第271條第1項,法院若無合理確信認有牴觸憲法之疑義,基於法秩序之安定性及權力分立民主憲政原則之尊重,自應做合憲解釋。而不能依司法院釋字第371號解釋意旨,裁定停止訴訟並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本院尚無死刑規定牴觸憲法疑義之合理確信:憲法之效力高於法律,法官有優先遵守之義務。本案適用之刑法第271條第1項(含刑法第33條第1款)死刑規定,上訴人雖認有違憲疑慮,但憲法第23條既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則如有上開必要,自得以法律限制。又自由權利之限制,該條既未規定僅限於一定期間內之自由權利限制,自得包括自由權利之永久限制即死刑在內(因無期徒刑仍有假釋規定之適用,不屬自由權利之永久限制)。民國元年3月10日公布施行之暫時新刑律(主要援用大清新刑律)、17年3月10日公布施行之舊刑法及24年1月1日公布之現行刑法,均有死刑規定,於35年12月25日國民大會通過憲法並於隔年實施後,並未改變。故死刑立法應合於憲法第23條之規定。至具體之合憲審查,詳如後述。上訴人聲請傳喚法律專家鑑定死刑是否違憲一節,尚無必要。兩公約內國法化後,對死刑規定之影響及死刑判決有無違憲問題:兩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第3條規定: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則上開公約、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均具有我國內國法之效力。至其與我國其他法律之效力位階如何,法無明文。於二者發生法律衝突時之適用順序,基於人權保障之法治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人權保障密度較高之兩公約規範。從而兩公約內國法化後,已生實質限縮刑法死刑規定適用範圍之效果。關於刑法死刑規定之闡釋、適用,應與兩公約之規定、解釋等合併觀察,方足窺其全貌。憲法第15條明定:人民之生存權應予保障。公政公約第6條第1項明定:「人人皆有天賦之生存權。此種權利應受法律之保障。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所指之「人民」、「人人」或「任何人」,應包括殺人案件之被告及被害人在內。其等生命價值,無高低差異,均屬無價,同被保護,不得被「無理」剝奪。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6號一般性意見書第3段指出:「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這是極其重要的規定。委員會認為,各締約國應當採取措施,不僅防止和懲罰剝奪生命的犯罪行為,而且防止本國保安部隊任意殺人。國家機關剝奪人民生命是極其嚴重的問題。因此,法律必須對這種國家機關剝奪人民生命的各種可能情形加以約束和限制」。足見,國家為「防止和懲罰剝奪生命的犯罪行為」,有「採取措施」的義務。而其措施,並不排除國家機關非「任意或無理」剝奪人民生命之情形,僅應嚴加約束與限制。2006年聯合國新聞部聯合國網頁事務科於聯合國官網公布之公政公約第6條中文版係謂「在未廢除死刑的國家,判處死刑只能是作為對最嚴重的罪行之懲罰,判處應按照犯罪時有效並且不違反本公約規定和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的法律。這種刑罰,非經合格法庭最後判決。不得執行。」足見該公約揭示:死刑判決是「對最嚴重的罪行(themostseriouscrimes)之懲罰」。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6號一般性意見書第7段謂:「themostseriouscrimes」這個詞要嚴格限定,《公約》規定的程序保證必須遵守,包括有權由一個獨立的法院進行公正的審判、無罪推定原則、對被告方的最低程度之保障和由上級法院審核之權利。第32號一般性意見書第59段謂:「在審判最終處以死刑的案件中,嚴格遵守公正審判的保障特別重要。審判未遵守《公約》第14條而最終判以死刑,構成剝奪生命權(《公約》第6條)。」足見死刑判決若符合公政公約所定之上開實質及程序上限制、拘束,即不構成公政公約第6條所指之「無理剝奪」生命權。從而,死刑判決是否違反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及兩公約,自應視其是否為最嚴重罪行,及有無踐行審判中程序保障為斷。非有公政公約第6條第2項所指之「最嚴重罪行」,並於遵守公正審判之程序保障,不得判處死刑。死刑判決之合憲性審查:1.最嚴重罪行(themostseriouscrimes)之界定:我國刑罰原則採「行為責任」,而非「行為人責任」;刑法係對某一「犯罪行為」,施以相對應之「刑罰」。犯罪行為是否符合公政公約第6條第2項所指之「最嚴重罪行」,如上所述,應嚴格限定。以死刑係「剝奪犯罪人生命」之刑罰言,「最嚴重之罪行」,至少必須是「無理剝奪他人生命」,或與之相當之其他極為嚴重罪名;然並非所有「無理剝奪他人生命」罪名之犯行,均當然係「最嚴重罪行」;基於「行為責任」原則,尚應考量與犯罪行為本身攸關之事項,是否已達最嚴重程度,方足當之。例如,其犯罪行為動機是否具倫理特別可責性(例如嗜血殺人魔、謀財害命、性癮摧花或其他卑鄙動機等)、犯罪手段或情節具特別殘暴性、行為結果具嚴重破壞性、危害性等。2.死刑之刑罰目的在處罰與一般預防,不及於特別預防:對於犯罪之「刑罰」,我國向認兼具「防治和處罰犯罪」之作用與功能。監獄行刑法第1條規定:「徒刑拘役之執行,以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足見「教化」係「無期徒刑、有期徒刑及拘役」刑罰之執行目的,尚非死刑或罰金刑之刑罰執行目的。又現代刑罰理論所謂「犯罪應報」,係指理性化以後之法律概念,是基於分配正義原則之作用,對於不法侵害行為,給予等價責任刑罰之意。此即以犯罪人之行為責任為基礎,使「罪與責相符、刑與罰相當」之真意。實與最原始之「同害報應刑思想」,即「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命還命」之概念有別。不能以我國不採「同害應報刑思想」,即否定我國刑罰具現代刑罰理論之「犯罪應報」作用與功能。故而,刑罰之目的就「處罰或懲罰犯罪」言,具犯罪應報及一般預防色彩;就「防治犯罪」言,具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色彩。死刑作為刑罰之一種,當亦存有現代刑罰理論之「犯罪應報」概念。辯護人謂刑罰之目的僅在預防云云,尚非的論。3.目的正當性之審查:每一個人之生命價值,均同等珍貴、無價,受國家法律之同等保障。除不容許國家機器「無理或任意剝奪」外,更不容許任何包括上訴人在內之個人「任意、無理剝奪」。基於「維護人性尊嚴及確保人格自主」乃現代法治國憲法之核心價值,而死刑刑罰之最終目的,在防止人民之生命權遭他人「無理剝奪」,使社會上每一個人之人性尊嚴與人格自主,得獲有效保障,此乃「極端重要之公益」,其目的自符合憲法第23條所指:「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之目的正當性要求。4.手段適合性之審查:法律規範係社會生活之產物,其解釋與適用不能與社會脫離。除法律有明顯漏洞或法官有違憲之確信時,法官才能造法或暫時停止法律之適用,而聲請釋憲。此外,適用法律之法官,有義務尋找最適合於當代社會需求之立法真意,使法律之適用與社會絕大多數人之是非觀或價值觀相契合,俾法律真正發揮其應有的規範功能,而具實效性,並謀求社會最大多數人之安全與福祉。現階段社會絕大多數人之價值觀或法意識普遍認為:每一心智健全之成年人,都應為自己任意、無理剝奪他人生命之犯罪行為負責;若有心智健全、復無其他歸因事由之成年人,可不負全責,無異表示該人享有侵害他人之特權,亦無異承認該犯罪人之人性尊嚴高於被害人;則社會秩序難以維持、公共利益難以增進,他人自由之妨礙或其他緊急危難,亦難以防止、避免。從而,當無理、任意剝奪他人性命之殺人犯行明確無誤,復無法定責任減輕事由,且依其犯罪行為動機具倫理之特別可責性、犯罪手段或情節具特別殘暴性、行為結果具嚴重破壞性、危害性,已達最嚴重罪行之程度時,依現代刑罰理論之「犯罪應報」思維,課以「罪與責相符、刑與罰相當」之死刑處罰,當能與上開社會絕大多數人之法價值體系或其所表彰之社會正義相契合。則社會一般人將更願意從內心服從法律,發揮法律之實效性,使每一個人同樣平等、尊貴的生命權,降低被模仿殺害(一般預防功效)或私刑正義犯罪歪風,增加生命權有效保障之機會。故而,死刑措施與其所欲達到之目的(即對最嚴重罪行之處罰與防治,以有效維護社會每一個人的生命權)間,具合理適當關係,且是有效手段,符合手段適合性之要求。5.手段必要性之審查:當「最嚴重罪行」之罪責極端嚴重,非課以死刑之處罰,不足以滿足「罪與責相符、刑與罰相當」之要求,亦無法符合上述社會上普遍認可之法價值體系及其表彰之社會正義時,則死刑以外之措施,將無法達到「處罰與防治最嚴重罪行」所欲達到之維護社會每一個人生命權之目的。此時死刑之措施即無其他替代措施,而得認符合比例原則之「手段必要性」要求。本件殺人既遂之犯罪事實,符合公政公約第6條第2項前段所定「最嚴重罪行」之要件。關於死刑部分之判決符合憲法第23條之規定,無違法或不當問題:依原判決所認上訴人如前揭犯罪動機、目的,犯罪時未受任何刺激,犯罪之手段,犯罪所生之危險及損害等情節觀之,其犯罪動機具倫理之特別可責性,犯罪手段或情節具特別殘暴性,行為結果具嚴重破壞性、危險性。原判決認殺人既遂犯行,符合公政公約第6條第2項前段所指「最嚴重罪行」,尚無違誤。辯護人謂「最嚴重罪行」係指符合「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定義之犯罪行為,方足當之云云,尚屬無據。法院依嚴格證據法則,調查證據、認定事實,於達超越合理可疑確信程度,而認定犯罪事實、適用刑事法規,而課以罪名後,在評價該犯罪應施予法律所許可之刑種及刑度時,首應依其「罪行」衡量出「與罪相符(等價)之責」,再依其「罪責」衡量、選擇「相應之刑」,及「與刑相當之罰」。俾符刑事審判在「實現分配正義」,及「刑罰」在「防治和處罰犯罪」之作用與功能,進而實現刑法之規範目的。至於確定罪行後衡量罪責時,應依刑法第57條為審酌。而該條所列尤應注意之10款事由,可區分為「與行為事實相關」之裁量事由(例如犯罪之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刺激,犯罪之手段,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及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及「與形成犯罪時之行為人自我相關」之裁量事由(例如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犯罪行為人之品行,犯罪行為人之知識程度,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後之態度)。關於「與形成犯罪時之行為人自我相關」之裁量事由,依一般人普遍具有之理性分析,又可依其係「明顯可歸因於外在(例如家庭、學校及社會)之事由」或「非明顯可歸因於外在之事由」,而有不同評價及衡量。即前者得為量處較輕刑度之事由,後者則否。就「與形成犯罪時之行為人自我相關」之裁量事由部分,原判決依卷內資料認定上訴人於行為時係屬心智正常之成年人,其生活成長過程,家庭功能健全、環境良好,父母關心,彼此能作有效溝通。求學過程中,在師長、同學眼中,表現均屬良好、正常。除課業成績、與同儕人際相處之枝節挫折外,未有生活上巨大變故。而國防大學理工學院之退學經驗,固係其壓力,然綜合上訴人所述及卷內資料顯示,自其國小起至大學中所受一切「人生奮鬥過程之挫折」而言,並未因此造成上訴人辨識其行為違法之意識能力或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控制能力,有所欠缺或顯著減低。則就「與形成犯罪時之行為人自我相關」裁量事由中,尚查無「明顯可歸因於外在之事由」,而得為量處較輕刑度之事由。就「與行為事實相關」之裁量事由部分,依原判決所認如前所示之犯罪動機、目的,犯罪時未受任何刺激,犯罪之手段,犯罪所生之危險及損害等情節觀察,本件殺人既遂犯行,已達最殘酷嚴重程度。就「與行為事實相關」之裁量事由中,亦無得量處較輕刑度之事由。上訴人應對其全部罪行負完全之罪責,當無疑義。上訴人殺人既遂罪行已達「最嚴重」程度,復應負完全責任,已如上述。依此部分罪行相應之罪責而言,堪認亦達「最嚴重」之程度。則依現代刑罰理論之「犯罪應報」思維,若非課以死刑之處罰,實無以滿足「罪與責相符、刑與罰相當」之刑責要求。亦無法符合上述社會上普遍認可之法價值體系及其表彰之社會正義,達到「處罰與防治最嚴重罪行」所欲達到之維護社會每一個人生命權之目的。且無法有效發揮刑法之社會規範功能。原判決就殺人既遂罪部分,均量處死刑,符合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無違法或不當可言。「教化」非死刑刑罰之目的:於依「罪行」衡量「與罪相符之責」,再依其「罪責」衡量、選擇「相應之刑」及「與刑相當之罰」後,認非處以死刑無法「實現分配正義」、或符合前述社會上普遍認可之法價值體系及其表彰之社會正義,達到「處罰與防治最嚴重罪行」之功用時,則該「死刑刑罰」之目的僅有「處罰及一般性預防功能」,而無「特別預防功能」存在,已如前述。從而「教化可能性」即非此時應予考量者。本件殺人既遂部分,尚無因「教化」目的而考量上訴人「教化更生可能性」之餘地(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984號刑事判決)。
瀏覽次數: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