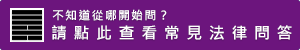民法上代理權外觀、表見代理與數位時代交易安全之重構
法令摘要:
民法第107條與第169條共同建構代理權外觀與信賴保護之核心體系。第107條限制代理權撤回對善意第三人之對抗力,第169條則透過表見代理,使本人對其創設或容忍之外觀負責。二者皆以權利外觀、本人可歸責性與第三人正當信賴為成立基礎。於數位與人工智慧交易環境中,帳號與系統成為身分外觀來源,惟表見代理不應僅以「過失」為門檻,而須回歸「有意識風險創設」之歸責結構。僅當外觀源於本人之行為或容忍,始得要求其承擔法律效果,藉以平衡交易安全與個人風險負擔。
(=民法第一百零七條=民法一百六十九條)
律師註釋:
導論:從「內部授權」走向「外部信賴」的代理法轉型
代理制度的核心功能,在於使本人得以透過他人之行為,參與法律關係並擴張其行為能力之射程。然而,代理制度同時亦蘊含風險:當代理權遭限制、撤回,或自始未曾存在時,交易相對人是否仍應承擔因信賴代理權而生之不利益?若本人得恣意以「內部授權關係」為由,否認代理行為之效力,則代理制度反而成為破壞交易安全的工具;反之,若凡外觀存在即一概拘束本人,又將過度侵蝕本人對自身法律關係之控制權。民法第107條與第169條,正是在此張力之中,試圖建構一套兼顧「本人控制權」與「交易信賴保護」的平衡機制。
民法第107條規定,代理權之限制及撤回,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民法第169條則進一步確立表見代理制度,於本人「由自己之行為表示授權」或「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時,令本人對第三人負授權人責任。二者共同奠立我國代理法之「權利外觀理論」基礎,使法律效果不再僅取決於內部授權是否存在,而轉以「相對人是否基於正當理由信賴代理權之外觀」作為評價核心。
此一體系,在傳統面對的是書面委任、公司職務名銜、印章使用等外觀問題;然於網路交易與人工智慧締約時代,代理權外觀已高度數位化,帳號、密碼、系統身分識別本身,即成為唯一可資信賴的「人格外觀」。冒名交易、帳號盜用、AI被入侵而締約,均使民法第107條與第169條的適用場域,從實體世界擴張至虛擬空間。此時,究竟應如何理解「權利外觀」、「可歸責性」與「善意第三人」?僅以過失即要求本人承擔授權人責任,是否已逾越表見代理原本的正當化基礎?抑或仍應堅守「有意識創設外觀」之門檻,以避免風險過度轉嫁於被冒名者?
本文即以民法第107條與第169條為中心,結合權利外觀理論、信賴保護原則與現代數位交易實務,系統性重構代理權限制、撤回與表見代理之法理基礎,並嘗試回應網路交易與人工智慧締約所帶來的新型風險配置問題。
第一章 民法第107條之制度定位:代理權限制、撤回與權利外觀理論
民法第107條規定:「代理權之限制及撤回,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但第三人因過失而不知其事實者,不在此限。」其立法意旨並非否認本人對代理權之處分權限,而是在於:本人既已透過授權行為,使代理權之外觀進入交易領域,即不得再以其與代理人間之內部關係變動,片面破壞第三人基於該外觀所形成之正當信賴。
立法理由已明確指出:本人於授與代理權後,固得加以限制或撤回,惟該等內部變動,原則上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此一規範,反映出代理制度由「內部意思理論」轉向「外部信賴保護」的現代趨勢。代理權不再僅被視為本人與代理人間的內部權能,而同時具有「對外公示效果」;一旦進入交易社會,即形成可供第三人信賴之權利外觀。
因此,民法第107條的適用,並非僅取決於「代理權是否曾存在」或「是否已被撤回」,而須進一步審查:第一,客觀上是否仍存在足以使相對人合理信賴代理權繼續存在之權利外觀;第二,該外觀之形成,是否可歸責於本人;第三,相對人是否基於正當理由而為信賴。唯有在此三要件同時具備時,方得限制本人以撤權或限制對抗第三人。
此一結構,揭示民法第107條實質上係權利外觀理論之具體化,而非單純之技術性規範。其價值選擇在於:交易風險應優先由「製造外觀者」承擔,而非由「信賴外觀者」承擔。本人既以授權行為向外界釋放代理權存在之訊號,即應負有維持該外觀之注意義務;若其未適當消滅外觀,即不得將風險轉嫁於善意第三人。
然而,該條並未走向「絕對信賴保護」。條文明確排除「第三人因過失而不知其事實」之情形,顯示善意並非僅指主觀不知,而須結合客觀注意義務。換言之,民法第107條所保護者,乃「正當信賴」,而非任何輕率或放任的信賴。相對人若於交易上有查證可能而怠於為之,即喪失其受保護地位。
此一設計,使代理權制度不致淪為風險無限外溢之工具,而仍維持交易參與者之基本注意義務。代理法因而形成三角結構:本人須對其創設之外觀負責,第三人須對其信賴行為盡合理查證義務,而代理人則居於二者之間,成為外觀運作的媒介。民法第107條正是在此結構中,劃定風險分配的第一道界線。
第二章 善意第三人之要件與本人可歸責性──「不知」不足以構成善意
民法第107條所稱之「善意第三人」,並非僅指主觀上「不知道」代理權已被限制或撤回之人,而是指在具體交易情境中,基於合理注意義務仍無從得知該事實,且其信賴具有正當性者。換言之,本條所保護者,並非單純無知,而是「正當信賴」。此一理解,係權利外觀理論與誠實信用原則交織下的必然結果。
若僅以「不知」作為善意之判準,則任何怠於查證之相對人,均可藉由主張「未曾聽聞撤權」而要求本人承擔風險,將使代理制度成為放縱交易懶惰的工具。是以,實務與學說皆指出,民法第107條之善意,應解釋為「相對人就代理權繼續存在具有正當理由信賴」。此一「正當理由」,須從交易類型、當事人身分、交易規模、過往往來經驗、是否存在足以引發懷疑之異狀等因素,綜合判斷。
例如,在長期商業往來關係中,代理人一向代表本人締結同類型契約,且本人從未表示異議,則相對人對代理權繼續存在之信賴,通常具有正當性;反之,若交易內容顯著超出以往範圍,或金額異常巨大,理性交易者本即應提高警覺,進一步確認代理權範圍。於此情形,若相對人仍逕行締約,難謂其信賴具有正當性,即屬「因過失而不知」,不受民法第107條之保護。
此一善意標準,實際上係在「交易效率」與「交易安全」間劃設界線:法律並不要求相對人於每一交易均進行全面調查,但亦不容其完全放棄合理注意。代理權制度因此內含一種動態平衡:本人負有消滅外觀之義務,相對人負有基本查證之義務,二者共同維持交易秩序之可預測性。
另一方面,民法第107條之適用,尚須本人就權利外觀之存在具有可歸責性。所謂可歸責性,並非僅限於故意或過失之傳統侵權概念,而係指本人之行為,客觀上足以使第三人形成代理權存在之合理印象,且該外觀之形成,係源於本人對交易秩序之影響力。此一要件,使民法第107條不致演變為「結果責任」,避免本人僅因偶然事件而承擔他人行為之後果。
例如,本人授權代理人後,對外長期以代理人名義處理事務,並未公告撤權,亦未回收相關證明文件,此即屬可歸責之外觀創設;反之,若代理權係因偽造文件、竊取印章、駭客入侵系統而被冒用,本人本無能力防免,且未以任何行為向外界表示授權,則權利外觀之形成並非可歸責於本人,即難以要求其承擔授權人責任。
由此可見,民法第107條之運作,實際上包含三重審查:其一,客觀上是否存在代理權之外觀;其二,該外觀是否可歸責於本人;其三,相對人之信賴是否具有正當性。唯有三者同時成立,始構成「代理權限制或撤回不得對抗第三人」之正當化基礎。此一結構,使代理法不致流於僵硬,而得依交易實態彈性調整風險配置。
更重要者在於,該條所呈現之規範邏輯,已不再以「內部授權關係」為中心,而是轉向以「外部信賴秩序」為核心。代理權是否存在,於對外關係中,不再是純然的事實問題,而是經由權利外觀與信賴保護所形塑的「規範性存在」。本人若容許外觀持續存在,即應承擔該外觀在交易社會中所引發之法律後果;相對人若無合理理由信賴,則須自行承擔其交易風險。
這樣的設計,使民法第107條成為代理法體系中連結「意思自治」與「交易安全」的關鍵節點,亦為後續表見代理制度的發展奠定理論基礎。
第三章 內部授權與內部限制──代理制度中的風險分配邏輯
代理權的授與,於法律結構上具有雙重面向:一方面,它是本人與代理人間的內部法律關係;另一方面,它同時向交易社會釋放「此人得以本人名義行事」的外部訊號。正因如此,代理權一經授與,即不再只是當事人私領域中的安排,而成為交易秩序的一部分。民法第107條所處理的,正是當本人在內部關係中對代理權加以限制或撤回時,該內部變動是否得以影響外部交易關係的問題。
在實務上,最具爭議者,莫過於「內部授權但內部限制」的情形。所謂內部授權,是指本人曾賦予代理人一定範圍的代理權;所謂內部限制,則是本人在授權時或授權後,於本人與代理人之間約定某些限制條件,例如不得超過一定金額、不得處分特定財產、不得與特定對象交易等。此類限制,若僅存在於內部關係,而未對外明示,則在代理人違反限制與第三人締約時,究竟應由誰承擔風險,正是民法第107條所要回答的核心問題。
依權利外觀理論之基本精神,只要相對人基於合理理由信賴代理權之外觀,且該外觀之存在可歸責於本人,則本人即不得以內部限制對抗相對人。此一結論,意味著內部限制原則上僅具有內部效力,不能當然影響外部交易。本人若選擇以代理制度參與交易,即須承擔「外部信賴優先於內部安排」的制度成本。
此一風險配置,並非任意偏袒第三人,而是基於交易效率與制度功能的理性選擇。代理制度之所以存在,正是為了降低本人親自出面交易的成本,並使交易得以迅速進行。若每一相對人於與代理人交易時,均須逐一查證其內部授權內容,代理制度將喪失其經濟意義。是以,法律選擇將內部限制的風險,原則上配置於本人一方,要求本人以適當方式消滅或調整外部外觀,而非將查證負擔全面轉嫁於交易相對人。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相對人可以完全免除注意義務。正如前章所述,民法第107條所保護者乃「正當信賴」,而非任何信賴。當交易內容顯然超出代理人通常權限,或存在足以引發懷疑之具體情事時,相對人仍應盡交易上必要之注意,例如要求出示授權文件、向本人確認、或要求補充說明。若相對人怠於為之,致其不知內部限制,則屬「因過失而不知」,自不在民法第107條保護之列。
因此,內部授權與內部限制的風險分配,並非單向傾斜,而是透過「權利外觀+正當信賴+可歸責性」三要件,形成一種動態平衡:本人負有管理外部外觀之責任,相對人負有基本查證之義務,兩者共同維持交易秩序之合理運作。
實務上亦多採此一立場。最高法院與高等法院判決屢次指出,代理權內部限制,原則上不得對抗善意相對人;但若交易顯屬異常,或相對人未盡基本注意,即難謂其為善意。此一見解,使代理制度既不致淪為本人規避責任的工具,亦不致成為相對人恣意冒險的藉口。
更深一層觀察,內部授權與內部限制之問題,其實揭示了現代私法的一項核心轉變:法律不再僅保護「內心真意」,而是轉而保護「在交易社會中可被合理理解的外觀」。本人之真意固然重要,但一旦其行為足以在外部世界形成一定形象,該形象即成為法律評價的對象。代理權制度,正是此一轉變最具體的展現之一。
在此脈絡下,民法第107條不僅是一條關於代理權撤回的技術性規定,而是現代交易法秩序的縮影:私法自治仍為基礎,但其運作必須服從於交易安全與信賴保護的結構性要求。這種「由內而外」的風險轉移,為後續表見代理制度的成立,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第四章 民法第169條──表示授權與容忍代理的制度意義
若說民法第107條處理的是「原本存在之代理權」在限制或撤回後,其效力如何對待善意第三人,則民法第169條所面對的,則是「自始並無代理權」卻因本人行為而產生代理權外觀的情形。此條文乃我國表見代理制度之核心,其功能在於:當本人以自己之行為,使他人得以合理信賴某人具有代理權時,即便該人實際上並無代理權,本人仍須對外承擔如同授權人一般的法律責任。
民法第169條規定兩種典型態樣:其一為「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其二為「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前者通常被稱為「表示授權」,後者則被稱為「容忍代理」。兩者雖在外觀形成的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其共同點在於:本人皆以其行為或不作為,使第三人得以形成某人具有代理權的合理信賴,並因此進入交易。
在「表示授權」的情形中,本人可能以書面文件、名片、公司職稱、對外公告、或長期實際行為,向外界呈現某人具有代理權的印象。例如,公司將某員工列為「業務經理」,長期允其對外簽訂契約;或本人在公開場合介紹某人「全權代表我處理某事」,即使其內心並未賦予完整代理權,對外仍已形成足供信賴的權利外觀。此時,法律評價的重點不在於本人內心是否真欲授權,而在於其行為是否足以使理性第三人合理相信代理權存在。
至於「容忍代理」,則更具警示意義。本人明知某人對外自稱為其代理人,且此種自稱並非偶發,而是反覆、持續地出現,卻未即時澄清或阻止,使第三人逐步形成穩定信賴。本人之不作為,在此被評價為一種「有意識的風險放任」,其法律效果等同於積極授權。正因本人得以輕易阻斷外觀卻選擇沉默,法律遂要求其承擔由此產生的交易風險。
表見代理制度的正當性,並非源於對第三人的單純同情,而是基於一種風險歸責邏輯:既然權利外觀係由本人之行為或可歸責的不作為所創設,則該外觀所引發之信賴風險,理應由本人承擔,而非轉嫁於無從辨識內情的相對人。此種歸責方式,正是權利外觀理論在代理制度中的具體實現。
然而,表見代理並非一種「無條件保護第三人」的制度。其成立,仍須符合嚴格要件。首先,必須存在客觀可觀察之權利外觀,使理性第三人得以合理信賴代理權存在。其次,第三人必須為善意,亦即不知且無過失不知代理權不存在。再者,該外觀之形成,必須可歸責於本人,亦即本人以其行為或有意識之不作為,創造或維持該外觀。若僅係第三人單方誤解,或純屬冒名者自行捏造,而本人並無任何可歸責行為,則無從成立表見代理。
正是在此「可歸責性」要件上,學說與實務逐步形成較為嚴格的理解。民法第169條第一種情形雖以「由自己之行為表示」為文義,但若僅因本人過失,未能妥善保管文件或資訊,而遭第三人冒用名義締約,是否即應負表見代理責任,長期存在爭論。較為嚴謹之見解認為,既然本條第二種情形要求本人「明知」他人冒名而不反對,則第一種情形之「表示」,亦應解釋為本人「有意識地」以其行為對外形成授權外觀,方具有正當性基礎。否則,僅以過失即課以與故意相同之法律效果,將使責任門檻過度降低,反而失去制度上的衡平。
此一理解,使表見代理的適用範圍維持在「本人主導外觀形成」的典型風險區域內,而不至於擴張為「任何冒名行為皆由被冒名者負責」。在傳統實體交易時代,此一界線尚不難維持;然而,隨著網路交易、帳號制度與人工智慧締約模式的出現,「外觀」的形成方式已與過往截然不同,表見代理制度遂面臨全新的壓力測試。這正是下一章所要面對的核心問題。
第五章 數位環境下的冒名行為與表見代理之再定位
在傳統實體交易中,代理權外觀多半透過書面授權書、職稱標示、長期交易慣行等方式形成,其可歸責性通常源於本人明確的行為或容忍。然而,進入網路時代後,交易身分的表徵逐漸由「人」轉化為「帳號」,而帳號的控制權則繫於密碼、憑證或生物辨識技術。此一轉變,使得代理權外觀不再僅由本人積極塑造,而可能因駭客入侵、釣魚網站、惡意程式或親友冒用而被「被動生成」。在此情境下,表見代理制度是否仍得不經調整地適用,遂成為代理法理現代化的關鍵課題。
以網路拍賣帳號為例,第三人若見某帳號長期以固定名稱交易,自然會合理信賴該帳號即代表其名義人。若該帳號遭他人盜用,冒名締約,交易相對人主觀上幾無可能辨識其真偽。形式上,確實存在可供信賴的權利外觀;問題僅在於:該外觀是否可歸責於帳號名義人?若名義人已盡合理注意義務,例如妥善保管密碼、使用雙重驗證,卻仍遭高技術入侵,則其實並未「有意識地」創造或維持該外觀。此時,若仍令其負表見代理責任,等同將所有網路犯罪風險轉嫁於被害人,顯然不符代理制度原本的風險分配邏輯。
因此,較為妥適的見解認為,數位冒名案件中,仍須回歸表見代理的核心結構:權利外觀、善意信賴與本人可歸責性。帳號本身固然形成外觀,但該外觀是否「可歸責於本人」,須進一步區分其形成原因。若外觀源於本人有意識之行為,例如將帳號、密碼交付他人使用,或明知親友長期以其名義交易而未制止,則其情形與傳統「表示授權」或「容忍代理」並無本質差異,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69條,使本人承擔授權人責任。反之,若外觀係因犯罪行為所「竊取」,本人既未授權,亦無容忍,甚至已盡合理防護義務,則欠缺可歸責性基礎,難以正當化表見代理之成立。
在人工智慧締約場域,此一問題更形尖銳。當使用者設定AI系統自動下單、議價或簽約,其行為本質上係以科技工具延伸自身行為能力,類似於「事前授權」的技術化表現。若第三人駭入系統,操控AI以使用者名義締約,則該表示並非源於使用者之意思。若使用者僅因技術漏洞而受害,卻仍須承擔契約責任,無異於將科技風險全面歸屬於個體,既不符合代理制度的歸責邏輯,亦不利於數位經濟的發展。
因此,在數位環境中重構表見代理的適用界線,應把握以下原則:第一,帳號或系統本身雖形成身分外觀,但僅屬「外觀存在」之要素,尚不足以導出本人責任;第二,須進一步審查該外觀是否可歸責於本人之有意識行為或風險放任;第三,僅在本人透過行為或容忍,使他人合理信賴其已授權時,方得類推適用民法第169條;第四,若僅屬犯罪入侵,且本人已盡合理防護義務,則至多成立締約上過失,甚至不生任何責任。
此種區分,並非削弱交易安全,而是將風險配置回歸其合理來源。交易相對人固值得保護,但其信賴若係建立在犯罪行為之結果上,而非本人所創設之外觀,則該風險不應由本人單方承擔。否則,代理制度將由「外觀可歸責原則」退化為「結果責任」,反而破壞其內在正義。
從此角度觀之,民法第107條與第169條所構築的體系,並非僅屬歷史產物,而是一套可隨技術變遷而調整運作方式的風險分配模型。其核心精神不在於形式上的「有無授權」,而在於:代理權外觀由誰創造?誰應對該外觀的存在負責?誰較適合承擔由信賴所生之風險?唯有緊扣此一結構,代理制度方能在數位與人工智慧時代中,持續維繫本人控制權、第三人信賴與交易安全三者之間的動態平衡。
第六章 民法第107條與第169條之交錯運作:權利外觀的生成、維持與消滅
民法第107條與第169條,表面上分屬不同規範層次:前者處理「已存在代理權」之限制與撤回對第三人之效力,後者則處理「原本不存在代理權」卻因外觀而使本人負責之表見代理。然而,二者在規範結構上實具高度同質性,皆以「權利外觀」與「信賴保護」為核心,並以本人之可歸責性作為風險歸屬的正當化基礎。其差異僅在於外觀形成之時間點與方式不同:第107條係處理「原本真實存在之代理權,其外觀延續於撤回或限制後」;第169條則處理「自始欠缺代理權,卻因本人行為或容忍而形成外觀」。
從體系觀察,第107條可視為「消極外觀責任」,亦即本人原本確實創設代理權,嗣後限制或撤回,卻未有效消除其對外所形成之外觀,因而須對善意第三人負責;第169條則屬「積極外觀責任」,本人以行為表示授權,或明知他人冒名代理而不反對,直接創設可供信賴之外觀。二者雖然在文義上各自獨立,但在風險分配邏輯上,實為同一原則的兩種展現:凡代理權外觀可歸責於本人,而第三人基於正當信賴而交易,則本人應承擔其法律效果。
正因如此,第107條所稱「善意第三人」,並非僅指主觀上不知撤權事實者,而應解釋為「對代理權繼續存在有正當理由信賴之第三人」。若相對人對代理權是否仍然存在,本可經合理注意即得知,卻怠於查證,則其信賴欠缺正當性,即不屬第107條所保護之範圍。此一解釋,使第107條實質回歸權利外觀理論之三要件:外觀存在、本人可歸責、相對人正當信賴。
在實務上,內部撤權或限制若未對外公告,且本人仍容許代理人持續使用名片、授權書、電子憑證或帳號進行交易,外觀顯然持續存在。此時,即便本人於內部已終止代理權,仍不得以之對抗善意第三人。反之,若本人已合理地消除外觀,例如公告撤權、回收授權文件、註銷帳號權限,或以交易慣行可得知之方式通知相對人,則權利外觀已不存在,第三人之信賴即欠缺正當性,第107條亦無適用餘地。
第169條在數位時代的功能,則呈現出與第107條更為緊密的互補關係。當本人未曾授權,卻因其行為或不作為而形成外觀時,第169條補足了第107條所無法涵蓋的情形。特別是在網路帳號、API金鑰、AI代理模組等情境中,外觀往往並非透過明示授權形成,而是經由「可持續使用之身分工具」所構成。若本人明知他人長期使用該工具以其名義交易,卻未加以制止,則其與傳統「容忍代理」並無實質差異,自應承擔表見代理責任。
然而,二條之交錯運作亦揭示一項重要限制:表見代理並非凡有外觀即成立,而必須以本人之「可歸責性」為界線。若外觀之形成或延續,並非源於本人之行為或風險放任,而係犯罪入侵、系統漏洞或不可抗力所致,則不論係撤權後之外觀延續,或自始不存在代理權之外觀生成,均欠缺歸責基礎。此時,將交易風險完全轉嫁於本人,反而背離代理制度「由外觀創造者承擔風險」之原則。
因此,民法第107條與第169條並非機械適用的形式規範,而是一套以誠信原則為底層邏輯、以權利外觀為運作核心的動態調整機制。其真正功能,在於引導法院於具體個案中,衡量下列三項因素:代理權外觀是否存在?該外觀是否可歸責於本人?第三人之信賴是否正當?唯有三者同時具備,始得使本人承擔代理行為之法律效果。此一結構,使代理制度得以在面對數位化、去中心化與自動化交易環境時,仍保有彈性與正義基礎,而不致淪為單純保護交易表象之僵化規則。
第七章 代理權外觀責任之界線:從「過失」到「有意識風險創設」的轉型
在傳統民法思維中,責任歸屬往往以故意或過失為判斷基準,表見代理亦時常被理解為「本人有過失致生外觀」的結果。然而,細究民法第169條之文義與體系,可發現其責任基礎並非一般侵權法上的過失,而是更為嚴格的「外觀創設歸責」。條文所列兩種情形——「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與他人」與「知他人表示為其代理人而不為反對之表示」——皆指向本人「有意識」地以行為或不作為,創造或維持可供第三人信賴的代理權外觀。此一設計,顯示表見代理並非單純以過失為門檻,而是要求本人對外觀的存在具有規範意義上的可歸責性。
此一理解,在數位與人工智慧時代尤具關鍵性。若僅以「過失」作為表見代理的成立基礎,則凡帳號遭盜、密碼被竊、系統遭駭,只要使用者未能證明自己已盡極致防護義務,便可能被認定對外觀之形成具有過失,從而承擔契約責任。如此一來,表見代理將由「外觀創設責任」轉化為「科技風險責任」,使被害人反而成為風險承擔者,與代理制度原本欲將風險歸屬於「外觀製造者」之理念背道而馳。
因此,較為妥當的解釋方向,應將第169條所要求的「可歸責性」理解為「有意識地創設或容忍外觀」,而非僅止於技術管理上的過失。亦即,本人須在規範上被評價為「選擇承擔風險」的一方,例如:將帳號交付他人長期使用、允許他人以自己名義對外交易、明知他人冒名行為卻消極不作為,或設計交易模式時刻意對外營造「已授權」之印象。此時,第三人信賴並非源於犯罪行為,而是源於本人之風險配置選擇,自得要求本人承擔其後果。
反之,若外觀係由第三人之非法侵入所創設,本人既未授權,亦未容忍,甚至已採取合理防護措施,則其僅係風險之被動承受者,而非創設者。此時,若仍令其負表見代理責任,將使第169條由「信賴保護規範」轉化為「無過錯責任」,不僅超出立法原意,亦將嚴重抑制數位交易與人工智慧應用之發展。
此一轉型,亦有助於重新定位民法第107條之適用邊界。代理權之限制或撤回,固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但其前提仍在於「外觀延續」可歸責於本人。若本人已合理消除外觀,卻因第三人偽造、駭侵而重建外觀,則該外觀之存在並非本人之風險選擇結果,自不應適用第107條。由此可見,第107條與第169條雖在文義上分屬不同類型,但在責任結構上,皆應回歸同一核心:外觀是否源於本人之有意識行為或風險放任。
此種理解,使代理制度得以從單純的形式規則,轉化為一套以風險配置為核心的規範體系。本人並非對所有以其名義出現之交易一概負責,而僅對那些「源於其自身決策所創設之外觀」負責;第三人亦非凡見名義即得主張效力,而須證明其信賴係建立在本人可歸責之外觀上。如此一來,代理制度方能在高度不確定的數位環境中,維持誠信原則所要求的均衡:既不使本人承擔其無法控制之犯罪風險,亦不使第三人因本人之風險創設行為而蒙受不測損害。
-民法-民總-法律行為-代理-代理權的消滅-無權代理-表見代理
瀏覽次數:4405